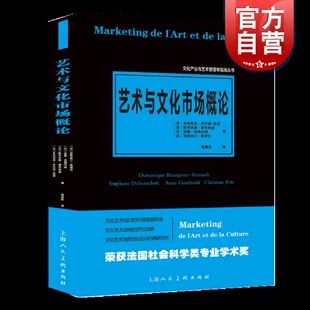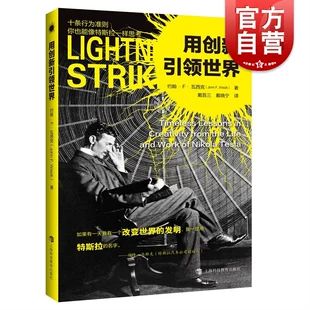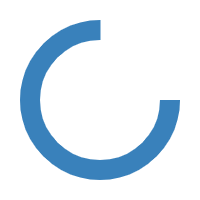
灵契 萨拉沃特斯 女版狄更斯 毛姆文学奖获奖作品维多利亚三部曲第二部哥特式悬疑指匠轻舔丝绒外国文学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Ссылка на оригинал- 100 — 1999 шт 5000$ за шт.
- 2000 — 50119 шт 4000$ за шт.
- 50120+ шт 3000$ за шт.
Проверка + фотоотчёт за 1.5$
Мы проверяем товар и делаем фотоотчёт, чтобы вы могли убедиться, что получите нужный товар без брака и повреждений.
Доставка из Китая в Украину, Узбекистан, страны Европы.
Оплачивается по прибытию на склад в Китае
Возврат товара возможен только пока товар находится у нас на складе в Китае. После отправки из Китая товар возврату не подлежит.
Фото и описание товара

| 产品展示 |
|
|
| 基本信息 |
| 图书名称: | 灵契 |
| 作 者: | [英] 萨拉·沃特斯 著 |
| 定价: | 56.00元 |
| ISBN号: | 9787208143098 |
|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开本: | 32开 |
| 装帧: | 精装 |
| 出版日期: | 2017-9-1 |
| 印刷日期: | 2017-9-1 |
| 编辑推荐 |
| ★“毛姆文学奖”获奖作;BBC英剧《指匠情挑》《轻舔丝绒》原著作者、当今首屈一指的讲故事高手,讲述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比死更冷”。 ★《每日邮报》赞其“作者写作功底深厚,读者对于她笔下的任何内容都会照单全收”。 ★一个身陷囹圄的灵媒,一位渴望自由的富家小姐,一群被时代困住的女人。 |
| 内容介绍 |
| 一个身陷囹圄的灵媒,一位渴望自由的富家小姐,一群被时代困住的女人。 富家小姐玛格丽特见到女囚塞利娜·道斯,惊为天人。她唤起了她对于被囚的痛感,对自由的渴望,对未知生活的向往。她无法控制地频繁前往监狱,对塞利娜关照有加,从同情到认同,从共鸣到爱意,玛格丽特对塞利娜的感情一发不可收拾。但这个谜一样的女孩,到底是信口雌黄的欺诈犯,还是天赋卓群的奇才? 《灵契》为萨拉·沃特斯维多利亚三部曲的第二部,是一部充满叙述力量和文字力量的作品,对女性身处的情感困境与社会困境的揭示深刻而尖锐。 |
| 作者介绍 |
| 萨拉·沃特斯,1966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文学博士。 三度入围“布克奖”,两度入围“莱思纪念奖”。 曾获“贝蒂·特拉斯克文学奖”、“毛姆文学奖”。 被《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为“年度青年作家”(2000)、文学杂志《格兰塔》选为“20位当代*好的青年英语作家”之一(2003)、“英国图书奖”评为“年度作家”(2003)等,文学评论界称其为“当今活着的英语作家中*会讲故事的作家”。 |
| 目录 |
|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
| 一、 我从未如此害怕。他们把我反锁在我的房间,四下漆黑一片,只能靠着点窗外的光写字。他们要露丝来锁门,她不肯,“什么?你们要我把主人锁起来?但她没干什么啊。”最后医生从她那儿拿来钥匙,锁上门,让她离开。现在屋里人声鼎沸,频频响起我的名字。要是闭眼去听,今晚其实与任何一个普通的夜晚没什么不同。我也许正在等布林克太太带我下楼去冥社,玛德琳或其他女孩子会在那儿,红着脸,想着彼得,想着他浓密的黑色胡须和泛着光的手。 但此刻,布林克太太正孤零零地躺在她冰冷的床上,玛德琳·西尔韦斯特在楼下号哭。彼得·奎克走了,我想是永远离开了。 彼得太过粗暴,玛德琳又太紧张。当我说我感觉他近了的时候,她只是不住地颤抖,紧闭双眼。我说:“只是彼得而已,你不怕他吧?这不,他来了,睁开眼,看看他。”她不听劝,只是说:“哦,我好怕!哦,道斯小姐,请不要让他再靠近了!” 当然了,很多女士第一次与彼得近距离接触时,都说过类似的话。听她这么说,彼得大笑,“怎么了?我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吃你的闭门羹?你知道我一路过来多艰辛吗?你知道为了你,我吃了多少苦?”玛德琳又哭了起来。当然这也不足为奇,确实有的姑娘会哭。我说:“彼得,玛德琳只是害怕而已,温柔一点,她会让你靠近的。”但当彼得轻轻地走上前,把手搭在她身上时,玛德琳发出一声尖叫,突然间身子僵直、脸色惨白。彼得问:“傻姑娘,你这是怎么了?这样不会有效果的,你还想变好吗?”但她只顾一个劲儿地尖叫,跌倒在地,乱踢乱蹬。我从没见过哪个淑女这样。我喊:“天哪!彼得!”他看了我一眼,扭头对玛德琳说:“你这个小贱货。”他按住她两条腿,我用手捂住她的嘴——我只是想让她消停会儿——挪开手时,手上却已血迹斑斑,她大概是咬了舌头或是把鼻子弄出了血。一开始我甚至没反应过来这是血,它如此漆黑,又似乎如此温润厚实,像是密封用的蜡。 即便满口鲜血,玛德琳还是凄厉地叫着,引来了布林克太太。走道里传来脚步声,她惊恐地喊:“道斯小姐,怎么啦?你受伤了吗?你哪儿弄疼了吗?”玛德琳听到布林克太太的声音,身子一扭,尖厉地叫道:“布林克太太!布林克太太!他们想把我弄死!” 彼得上前就是一巴掌,玛德琳了无生气地瘫在了地上。我想我们可能真的把她弄死了。我说:“彼得,你做了什么?快回去,快!”他朝柜子走去,这时,门把手一阵响动。门开了,布林克太太站在门口。她带上了自己的钥匙,手里拿着一盏灯。我说:“快关门!彼得在这儿,光线对他不好!”但她只是说:“怎么了?你们做了什么?”她看看僵硬地躺在客厅地板上、披头散发的玛德琳,又看看衬裙被扯破的我,再看看我手上并非黑色的鲜红血迹,又望了望彼得。彼得用手挡住脸,喊道:“把灯拿走!”他的长袍掀开,露出了白色的腿。布林克太太一直没动弹,最后提着灯的手开始颤抖。她“哦”了一声,朝我看,朝玛德琳看,手捂胸口,“不会她也……?哦!妈妈,妈妈啊!”她把灯放在一边,脸贴着墙壁,我走到她边上,但被她推开了。 我回头看彼得时,他已经不见了。只剩沾着他银色手印的黑色门帘微微颤动。 不过,死的毕竟是布林克太太,不是玛德琳。玛德琳只是晕了过去。她的女仆给她穿上衣服,带她到另一个房间,我听到她在那儿徘徊、哭泣。但是布林克太太越来越虚弱,最后完全站不住了。露丝赶来,喊道:“怎么了?”扶她躺到沙发上,紧紧握着她的手,说:“您会好起来的,别担心。瞧,我在这儿,爱您的道斯小姐也在这儿呢。”布林克太太看上去像要说话,却发不出声。露丝见状,说我们必须叫医生来。医生检查时,露丝一直握着布林克太太的手,啜泣着说她一定能挺过去。但布林克太太不久就咽了气。露丝说,除了喊妈妈,她没再说出一个字。医生说临终的女士常常会变得像孩子一样。他说布林克太太的心脏水肿得厉害,肯定一直都很虚弱,能活这么久已经是奇迹了。 他本来可能并不会费心过问布林克太太受惊的原因,谁知西尔韦斯特太太来了,她让他去看玛德琳。玛德琳的身上有一些印痕,医生一看,低沉地说,这事比他想的要古怪。西尔韦斯特太太说:“古怪?我看这简直是犯罪!”她叫来了警察,他们把我反锁在房间里,问玛德琳谁弄伤了她。她说彼得·奎克。警察问:“彼得·奎克?彼得·奎克?你在想什么啊?” 屋子里没有生火,虽然现在还是八月,我却觉得寒冷刺骨。我想我再也感觉不到温暖了!我再也无法平静,再也无法做自己了!我环顾房间,却看不见一件属于我的东西。布林克太太院子里的花香,她母亲桌上的香水味,木头上的上光剂,地毯的颜色,我给彼得卷的烟,珠宝盒里首饰的光泽,镜子里自己苍白的脸,似乎都变得陌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回到贝斯纳尔格林,回到我那爱坐在木头躺椅上的小姨身边。我甚至宁愿回到文奇先生旅店里我那面朝秃墙的房间。我愿意千百次地回到那儿,也不愿待在这里。已经很晚了,水晶宫的灯熄灭了,只看得见它那掩映于天幕的巨大黑色轮廓。 警察在盘问,西尔韦斯特太太嚷嚷着,玛德琳哭哭啼啼。布林克太太的卧室是整栋房子唯一安静的地方。我知道,她正孤零零地躺在黑暗里,笔直地躺着,一动不动,头发放了下来,身上盖着毯子。她也许正侧耳倾听这些叫嚷声、哭喊声,可能还希望张口说话。我知道她会说什么。我对她要说的太熟悉了,我甚至可以听见她要说的。 她悄然的话声,只有我听得到,这是所有声音里,我最害怕的。 二、 过了一会儿,发生了件古怪的事。 我站在下一排囚室第一间的门口,肩旁就是这间囚室的检查口或所谓的“牢眼”,上方钉着一块搪瓷板,记录着这个囚犯的罪名。要不是这块板,我还以为里面空无一人。这个房间似乎散发着一种奇特的静滞的气息——一种似乎比米尔班克所有的躁动都要深邃的寂静。正当我思忖着这气息时,寂静被打破了。一声叹息打破了这种寂静,一声简单的叹息——对我来说,那是一声完美的叹息,像是故事里的叹息,如此熨帖我当时的心境,奇怪地直击我心。我忘了里德利小姐和杰尔夫太太,她们随时都可能过来继续领路。我把那个不够警惕的看守与削尖的木勺的故事抛在了脑后,挪开铁片,把眼睛凑了过去。我看到一个女孩坐里面,她的姿态是如此安静,我屏住呼吸,害怕会惊扰到她。 她坐在一把木椅上,头后仰着,双目紧闭。女红放在腿上,双手松弛地扣在一起,窗口的黄色玻璃充溢着明亮的阳光,她面朝阳光,希望汲取一些热量。土黄色裙子的袖口歪歪扭扭地缝着一颗毛毡布做成的星,这是监狱等级的徽章,阳光一照,分外引人注目。她的帽檐露出几缕头发,十分秀美,她的眉毛、嘴唇与睫毛轻轻地缀在苍白的脸上。我确信,她与克里韦利画的圣人或天使有几分神似。 我大约打量了她一分钟光景。她自始至终闭着双眼,头颅静止不动。她的姿态里似乎带着一些虔诚的东西,一种静默……最后我终于意识到,她在祈祷!我突然感到一阵羞耻,正当我准备移开目光之时,她动了动,张开手掌,抬到面前。在她因劳作而变得粗糙的粉红色掌心里,一抹色彩掠过我的眼前。在她的指间,有一朵花——一朵紫罗兰,根茎已经有些耷拉。只见她把紫罗兰放到唇边,在上面轻呼了一口气,紫色的花瓣发出一阵颤动,似乎舒展了…… 看着她这么做,我才意识到她所处的世界是多么晦暗:这些牢房,这些被关押的女人,看守,甚至是我自己,我们的生活画布上尽是惨淡的兑了水的颜料,而这里唯一的色彩,仿佛是不小心落在上头的。 当时,我并没有纳闷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阴暗的地方,一朵紫罗兰会落到这双苍白的手中。我只是突然害怕地想到,她能犯下什么罪呢?我想起了那块悬在一旁的搪瓷板,悄悄关上检查口,读着上面的字。 上面有她的囚号、等级,下方写着她的罪名:欺诈行骗人身伤害。入狱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十一个月之前,她被判四年有期徒刑。 四年!在米尔班克待上四年,一定非常漫长吧。我想走到她的门口,叫她过来,给我讲讲她的故事。但这时,第一段走廊的那一头传来里德利小姐的声音,她的靴子摩擦着牢房寒冷的石板路上的沙粒。我犹豫了。我想,要是看守也发现女孩手里有花,她们会拿她怎样?我肯定她们会把花拿走,要是她们这么做,我会深感遗憾。于是,我走到她们看得到我的地方,在她们走近时说——当然也是实话——我有些累了,第一次参观,已经看到了我想看的。里德利小姐只是答了一声“好的”就带我回到走廊。这个牢房区的门在身后关上,我又回头张望了一下那个转角,心里半是满意、半是尖锐的遗憾。我心想,可怜的人儿!下周我来时,她还会在这里。 看守带我来到塔楼,我们小心地沿着螺旋向下的楼梯,走到更低洼、更阴郁的牢房区。我感觉自己像但丁似的,跟随维吉尔进入了地狱。我先是被转交给曼宁小姐,而后转给一个男看守,再被带着穿过五角大楼的二号楼和一号楼。我给希利托先生留了个口信,被带出监狱的内门,沿着楔形的沙石地往外走。监狱的高墙似乎在我面前不情愿地分开了。阳光比刚才更为强烈,也让瘀青色的阴影更显幽深。 我和看守并肩走着。我望着这片沉郁的监狱大地、贫瘠的黑色泥土和一块块蓑衣草,我问:“这儿是不是种不了什么花?有没有雏菊、紫罗兰之类的花呢?” 他说,没有雏菊,没有紫罗兰,甚至连蒲公英都没有。它们没法在米尔班克的泥土上存活。这里离泰晤士河太近,“和沼泽地差不多”。 我说我猜也是。思绪又回到了那朵花上。也许在女囚监狱的墙壁上,砖块间,能有那么些缝隙,可以让这样的植物扎根生长?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思忖这事很久。看守带我走到大门口,看门人为我叫来马车。所有的牢房、门锁、阴影、监狱生活散发的恶臭,便统统在我身后了,真的很难不为自己的自由而心怀感激。我想,也许,我决定去一趟米尔班克是个正确的决定。我很高兴希利托先生对我的过去一无所知。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些女人什么都不知道,我的过去可以安放在原来的地方。我想象他们拿着皮带把我的过去死死捆紧、牢牢扣好…… 今晚我和海伦说了话。我哥把她带来了,一起来的还有三四个他们的朋友。他们穿得十分隆重,准备去看戏。海伦身着灰色的礼服,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到时,我下了楼。与米尔班克以及我房间的寒冷寂静相比,这群人高谈阔论的声音、扬扬自得的脸庞,让我格外不适。海伦陪我走到屋子相对僻静的角落,我们简单地聊了聊监狱之旅。我向她描述了监狱千篇一律的走廊,说穿行其中让我分外紧张。我问她记不记得勒·法努有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女继承人遭人陷害,被人弄成疯了的样子。我说:“我真的想过,要是母亲与希利托先生暗中勾结呢?要是希利托先生打算把我弄得找不到北,关进监狱呢?”海伦听罢,笑了笑,但也看了下四周,确保母亲听不到。我又和她说了点女囚的故事。海伦说女囚一定很吓人,我说其实她们一点也不吓人,只是意志薄弱罢了,“总之,希利托先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要给她们带去好的影响。这是我的任务。她们会从我这儿学到优秀的品质。” 她一边听我说,一边看着自己的手,转动着手指上的戒指。她说我很勇敢。她肯定这份工作会帮助我从“所有过去的悲伤”中走出来。 母亲问,我们为何如此严肃、如此安静?今天下午我把牢房的情况说给她听,她听得浑身发抖,告诫我有客人时,千万不要跟他们讲监狱的细节。她说:“海伦,你可不要让玛格丽特给你讲那些监狱故事。你丈夫在等你呢,你们看戏要迟到了。”海伦立刻走到斯蒂芬身边,斯蒂芬握起她的手,吻了一下。我站着,看着他们,然后溜了上来,回到自己房间。我心想,要是我不可以谈论我的见闻,至少可以写在日记里吧…… 现在我写了二十多页。我读了一遍自己写的,感到我的米尔班克之旅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曲折。这次监狱之旅,比我扭曲的想象要干净得多!而我上一本日记里,尽是那些扭曲的东西。至少这次,这本不会再像上一本一样了。 已经十二点半了。我听得到阁楼楼梯上女仆的动静。厨娘把门插好——从今往后,这个声音听上去都不同了! 博伊德关上她的房门,走到窗口拉上窗帘。我的天花板仿佛是玻璃做的,她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真切。现在她解开了靴子的鞋带,让它们咚的一声落在地上。床垫咯吱作响。 窗外是泰晤士河,糖浆似的黝黑。那是艾伯特桥的灯光,巴特西的树,没有星辰的天空…… 一小时前,母亲拿来药。我说我想再坐一会儿,希望她把瓶子留下,我一会儿喝。她不依,说我“那病”“还没完全好”。还没有好。 我只得坐着,任她把药片倒入杯子。母亲一边看着我吞下药水,一边点头。现在我太累了,写不动了——但还是焦躁万分,睡不着。 里德利小姐是对的。当我闭上眼,我就能看见米尔班克寒冷苍白的走廊与一道道囚室的门。不知那些女人在那儿感觉怎样。我想到了苏珊·皮林、赛克斯、在鸦雀无声的塔楼里就寝的哈克斯比小姐,以及那个手捧紫罗兰的女孩,那个面庞如此精致的女孩。 不知她叫什么名字。 …… |
..
 .....
..... .....
.....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
 Nigeria
Nigeria